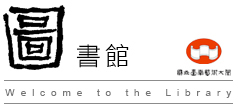10月【情結:內心隱形的拉扯力量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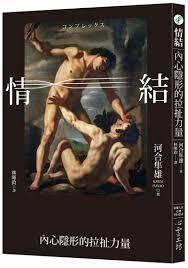
書名:情結:內心隱形的拉扯力量
作者:河合隼雄(Kawai Hayao)
館藏索書號|175.7 8467
館藏條碼號|C0137214
館藏地點| 四樓中文一般書區
ISBN|9789863574453
作者:河合隼雄(Kawai Hayao), 1928-2007
出生於日本兵庫縣,畢業於京都大學數學系。1962年赴瑞士蘇黎世榮格學院學習,是第一位取得榮格分析師資格的日本人。持有世界沙遊學會執照,為該會創始人之一,也是日本沙遊治療的主要推動者。曾任京都大學教育學院院長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長、日本文化廳廳長、日本臨床心理醫師學會會長、京都大學榮譽教授等職。
河合隼雄以深厚的心理學知識為基礎,長年針對日本文學、政治、教育、社會問題等不同領域進行論述、對話。著作甚豐,其中《日本人的傳說與心靈》一書曾榮獲大佛次郎獎,《高山寺的夢僧》榮獲首屆新潮學藝獎。其他重要著作包括《孩子與惡》、《轉大人的辛苦》、《青春的夢與遊戲》、《故事裡的不可思議》、《閱讀孩子的書》、《閱讀奇幻文學》、《佛教與心理治療藝術》、《源氏物語與日本人》、《神話心理學》、《民間故事啟示錄》(以上皆由心靈工坊出版)、《活著,就是創造自己的故事》(與小川洋子合著)、《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》(與村上春樹合著)、《原來如此的對話》(與吉本芭娜娜合著)、《走進小孩的內心世界》、《心的棲止木》等。
譯者:林暉鈞
畢業於國立藝專,為國內知名小提琴家。醉心哲學與當代思潮,2011年起引介並翻譯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著作,已出版《力與交換模式》、《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》、《作為隱喻的建築》、《移動的批判》、《帝國的結構》、《哲學的起源》、《世界史的結構》、《倫理21》、《柄谷行人談政治》。另譯有《神話與日本人的心》、《高山寺的夢僧》、《革命的做法》、《孩子與惡》(以上均由心靈工坊出版)等書。
推薦序
「情結」不只是「情結」:撥開「複雜性」的迷霧
魏宏晉(實踐大學兼任助理教授、《榮格心理學指南》譯者)
河合隼雄先生精通精神分析,深諳日本文化,卻也還得用一整本書的篇幅,佐以旁徵博引,輔助案例對照理論,才足以清楚解釋日譯後的「complex」一詞,足見精準把握此字原旨要義之不易。
日本學界譯介西方學術名詞,常使用漢字以補日語假名音譯稍遜形神之憾,而由於字義直通,應節合拍,許多便為華人學界直接因襲,比如,哲學、心理學、精神分析等,毫不違和。然而,在翻譯「complex」時,華文學界的用法和日本的有了分歧,日本最終以片假名音譯作「コンプレックス」;在中文裡,如今則通用為「情結」。不管是「コンプレックス」或者「情結」,都已經在各自的社會裡生根發芽,借河合先生的話就是「幾乎完全融入了日本人(中國人)的日常生活」裡。
本書首章開宗明義便直指該詞在日本的翻譯歷史,河合先生畫龍點睛地暗示了「complex」的概念並不一般,「最初這個用語被介紹到日本時,曾經有『心的複合體』或是『複合』等翻譯,目前則直接音譯」;一樣地,「complex」的概念被引介入中國之初,也曾經過反覆砥礪,不同的翻譯方式,代表譯者各自的理解或者重視的面向。
一九二一年,朱光潛先生在上海《東方雜誌》發表〈福魯德的隱意識說與心理分析〉一文,允為中國比較詳盡介紹精神分析理論之濫觴,但該文沒有提到「complex」的概念。朱先生稍後寫作《變態心理學》,介紹包括佛洛伊德等學者的心理學學說,一九三〇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。書裡,他將「complex」譯為「情意綜」,對後來有比較大的影響。高覺敷在一九三三年翻譯出版的《精神分析引論》(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)中,特別於卷首撰寫「譯言」,對幾個翻譯關鍵詞做出說明:「關於譯名,我所用的都較為普通,然而下列數詞卻有聲明的必要:『complex』有譯為『心組』的,我則譯『情意綜』,此詞為吾友朱君孟實所創,不敢掠美 。」
孟實為朱光潛先生的字,至於選譯作「心組」的是余文偉,一九二六年,他在上海《民鐸》上發表〈佛洛特派心理學及其批評〉長文,評介佛洛伊德理論。
此外,一九二〇、三〇年代,還有謝六逸與契可親採用「錯綜」的譯法。到了一九四〇年代,心理學家潘光旦翻譯英國性學家靄理士(Havelock Ellis)的《性心理學》(Psychology of Sex),特別在文中譯註裡指出:「精神分析派常用的『complex』一字,有人譯為『癥結』,也有人說,可以譯做『疙瘩』,都可以過得去,今酌定用『癥結』。精神上郁結不解的『癥結』,與普通行文時所用的『癥結』,例如,問題的癥結,自是不同,讀者自可參照上下,自可不致相混。」
台灣在一九六〇年代末引進精神分析理論,起初翻譯「complex」也有見選用「癥結」的,但很快地,「情結」的用法便流行了,與此同時,「情意結」與「情意綜」也間或可見;而中國大陸地區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改革開放後,重啟西方思想的正常譯介,就算重版早期著作,也都統一改為「情結」,比如一九八六年潘光旦的《性心理學》,以及一九八七年高覺敷的《精神分析引論新編》等簡體字重版,內文的「complex」都改譯為「情結」,這可能與官方統一外文譯詞標準有關。
引進新的外語詞條,譯法通常有段「百家爭鳴」的時期,因此「complex」起初有多種譯法,各國皆然,無可厚非。有趣的是,日本最後選擇了音譯,而台灣與大陸終究卻以「情結」為依歸,何以如此?「情結」看來望文差可知意,「心似雙絲網,中有千千結」,古典與雅緻兼之,日本人何不「從善如流」?
河合先生在他書中沒有直接觸及這個問題,畢竟他著書目的不在考據,但長篇論述,卻也足以說明此事與不同文化的語言字義轉譯後,無法「一言以敝之」有關。榮格原本使用「complex」的脈絡是指「情感複合體」(德語:gefühlsbetonter Komplex),是用以說明「某種情感集結而成的心理內容集合體」,它不只是望文生義的「情結」,單指一股憋在某處而無可伸張的胸中鬱結,而是可能有很多股情感集合醞釀,交互作用的結果。因此,「complex」的內涵是動態的「複雜性」(complexity),會產生情感的複雜性系統互動,如人腦、氣候、生態,甚至到整個宇宙,都是複雜性系統,皆具自發「湧現」(emergence)新現象的能力,本質上都是難以建模的系統。
也就是說,根據複雜性理論,作為心靈活動的關鍵點或樞紐的「complex」,基本上是難以掌握與預測的。它存在無意識當中,有如另一個(或者多個)活生生的人格,這種「另一個我」的現象包括內心感到分裂、雙重人格以及分身等,與意識自我(ego)並存,對心靈的運作(包括行為、情感和人際關係等)產生顯然地深遠影響,正如同榮格所說的:「(『complex』是)心的生命的焦點,也是節點,絕對不能消失不見。因為一旦『complex』消失,心將停止活動。」
因此,「complex」這個精神分析外來語,除了一「此無故」,本土自來無有,尚兼以「含多義故」,意義紛歧,不僅無法以病理化的「癥結」以偏概全;簡化為單純心理現象排列組合的「心組」自亦不宜;「錯綜」的形象有餘而內涵不足;至於「情意綜」雖然顧及情緒與意念交織形成的心理複合體之意,強調多元素動態交織,但是少了望文生義的文化形象;反而簡化其相似用詞,捨動態而就形象的「情意結」為「情結」來得簡單可親,或許這就是「情結」得以風行的緣故吧。
然而,「情結」雖以字義浪漫易解勝出,卻稍遜精義神髓。河合先生深知問題癥結,「……了解這個用語正確意義的人,也出乎意料地少。這是我想要重新思考『情結』的原因」,他「重新思考」的精華結晶正是本書。
本書初版於半世紀前的一九七一年,歷經五十年,久陳依舊彌新,仍然值得細品。對於「complex」,我們一知半解,惟閱讀本書後,經過榮格專家河合先生深入淺出地解說,終將恍然大悟,原來「情結」不只是「情結」,有若自「複雜性」的迷霧中甦醒。
資料來源 博客來網路書店、金石堂網路書店